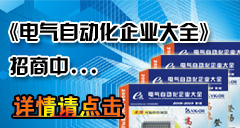| 【摘 要】财政分权体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在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日本、德国“二战”以来财政分权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都采取了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但是也存在着有待改进的方面。两国的经验对深化和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日本;德国;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地方经济;均衡发展
财政分权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热衷研究的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财政分权治理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目前,针对这一研究内容具有比较明显的争议,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政府间公用品供给效率提高和增进分配公平。日本学者神野直彦认为,财政分权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状况。[ 1 ] Oates ( 1972 ) , Bahl 和L inn ( 1992 ) 等认为,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
Tiebout (1956)认为,流动能力可以促使人们选择公共服务和税收的组合令其满意的社区,进而得到理想的公共服务水平。[ 2 ]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在实现地方经济的效率与促进公平方面并没有发挥作用。Harvey Rosen ( 2006)认为,联邦制虽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然而,效率和公平也可能要求中央政府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只用地方财力为地方公用品筹资,这种制度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3 ]斯蒂芬·贝利( 2006)认为,地方政府倾向于强调服务产出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涉及服务质量问题的灵活性、选择性及其它方面的问题几乎无人关注。[ 4 ]可见,财政分权的初衷在于解决多级政府的公用品供给水平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效率与公平分配,进而提高社会福利,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成为了财政分权实施绩效的反馈。
日本、德国都选择了多级财政分权体制。早在19世纪末期,随着市制町村治和府制郡制的正式形成,日本就形成了早期的分权力的财政管理体制。[ 5 ]而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确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目前,日本财政分权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相比较而言,虽然德国政府由联邦和州(州本级和地方)两级构成,地方政府不是联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层级,而只是州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德国传统中,地方政府有两个层次构成:一个是最底层的乡镇( communes) ;另一个位于底层之上的(市)县( counties or city counties)级地方政府。[ 6 ]但是,根据德国《基本法》,联邦、州和市镇三级政府都自行负责本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因此,本文力求通过对比日本市町和德国(市)县的基本情况,分析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日本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作用机制二战后,日本确立了财政管理体制,明确了中央、地方的财政管理权限,构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财政分权体制。
第一,中央集权与地方有限分权的财政分权体制。日本虽然实行了分权制财政框架,但日本属于中央集中立法,地方自治是由中央政府赋予的,地方权限的大小由中央确定,地方财政管理范围由中央确定,在财政政策、收支调整以及预算划拨等多方面体现了中央政府立法权利的宽泛和权威。而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府则没有立法权限,包括税收立法权在内的财政管理权限都由中央立法所规定,地方仅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具有选择权。
比如日本《地方税法》规定了市町村可以征收的地方税税目,要求地方政府在此范围内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可征收的地方税课税对象、税目、计税依据以及确定税率。中央政府规定了标准税率和税率变动幅度,地方政府如果不按照《地方税法》规定的标准税率征收,则必须上报中央政府;只有在一定范围内,地方政府才能自主选择。上述财政管理权限的确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主导型经济体制所具有的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可以清晰地传达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避免了中央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和产业规划中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噪声”。
第二,以税种分享作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渠道。日本正常财政收入的95%以上来自于税收,在多级政府间明确规定了税源划分原则。概括而言,日本中央和地方税源划分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 [ 7 ]一是以事权决定财权,“各级政府事务所需经费原则上由本级财政负担”;二是便于全国统一征收的大宗税源归中央,而相对零散的小宗税源划归地方;三是涉及收入公平、宏观政策的归中央,而体现收益原则的税源归地方。通过以上原则,界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根据以上原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税种。按照这种划分,固定资产税、特别土地使用税、城市规划税、事业所税等税收都纳入市町村财政收入。①通过合理划分收入来源渠道,为各级政府公用品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基础性物质保证,提高了日本公用品供给的效率,为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确立了基础和前提。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日本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图1所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地方政府、特别是市町村一级的税收收入比重明显提高。一方面,反映出税收收入分配向基层级政府倾斜的倾向;另一方面,本着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财力用于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职责与高企的债务赤字负担。事权决定财权,日本预算管理体制实行法治化管理,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公用品的责任。具有全国性、普遍意义的事权划分为中央,如国防、外交和公安等;都道府县则主要负责如港湾等公用品的管理;而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如消防、城市规划、卫生、住宅等则由市町村负责。同时,日本政府还规定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事权。地方政府更加贴近居民,可以根据本地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适当的公用品;同时,也可以结合本地的特殊性发展相关产业,并提供本地企业相应的政策,间接地降低了地方性企业的运营成本,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效率。然而,日本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渐膨胀, 债务负担日渐加剧,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远超10% ,在发达国家里面处于前列。鉴于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经济景气初现而经济增长式微,地方财政负担在短期内仍旧无法得到有效改善。
第四,以“两税一金”为主控的财政转移传导机制。日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事权需要,所需资金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资金转移。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地方交付税、地方让与税和国库支出金三种,将资金来源属于中央级的财政收入,通过同源分割、核定科目或者委托责任等方式,由中央政府直接向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分配,以平衡和弥补地方政府履行事权的资金缺口。
三种转移传导方式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接近1 /3。通过这种方式,不但有效地平衡了不同发达程度的地方政府资金需求,促进地方横向分配公平,而且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和公用品供给效率,也促进了地方所属企业的发展和本地区特色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综上可见,日本财政分权体制在促进政府间协调配合、提高公用品使用效率、平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地方经济景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在支出领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8 ]同时,在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公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走出“泡沫经济”的泥潭,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扩大,财政状况恶化,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十分窘迫。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来,小泉政府推行财政结构改革,在2004年启动了“三位一体”的财政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虽然也调整了一定的税收收入结构,但是其对地方经济的冲击尚有待观察。
二、德国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德国财政分权体制主要遵循1969年改革进行的,其主要目标在于:一是引导区域间经济活动,确保经济健康发展;二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福利提高。作为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德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集权框架下均衡财政分权体制。德国的财政管理权限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德国联邦立法机关不仅对归属于联邦政府的税种有立法权,并且对于州以下财政职能也同样拥有优先立法权。州以下政府在不与联邦立法权相冲突的情况下,在联邦专有的立法权限范围之外,经过联邦法律明确授权后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比如,地方政府所获得的税收总量由联邦议院认可,在州立法所确定的限度内,地方政府财政调整其在土地(财产)和工商业税方面的税率。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立法权限依托于联邦和州。同时,地方政府在保证预算平衡的前提下维持财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根据德国《基本法》,德国地方政府与联邦、州政府“收入共享”,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础因宪法规定而不可剥夺,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具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又要求联邦、州、地方(市镇)自行负责财政收支平衡。地方政府通过有针对性的引导,协调和管理地方企业、区域内流动资产等,发展本地经济和提高福利水平。
第二,同源共享的政府间财政收入利益共同体。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以税收和收费构成,其中,税收在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规模为95%左右。[ 9 ]在1969年的“财政大改革”之后,原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中央与州以下)分开征税的原则基本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税收共享制”。从收入分配形式看,德国是典型的以共享税为主、共享税与专享税并存的类型,即主体税种收入在联邦和州以下多级政府之间同源共享,共享税收入占一般税收总额80%以上,其所得税、增值税为联邦和州以下各级共享。②税收收入划入相应的财政预算级次。德国这种以主要税种作为主体进行分配的分税体制,客观上形成了各级政府间的利益共同体,保证了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中的主体地位,有效调动了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提供公 |